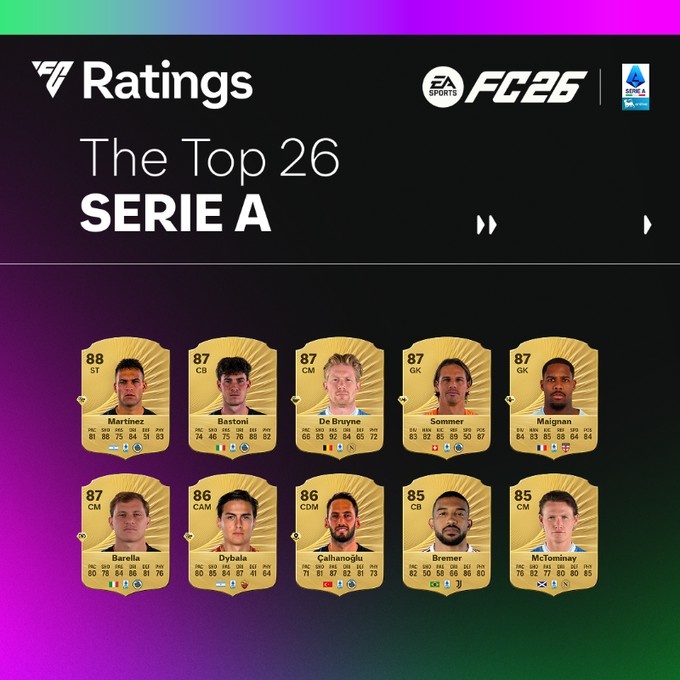原文标题:【少数派报告】红星之下的第比利斯迪纳摩,第比利斯迪纳摩
原文标题:【少数派报告】红星之下的第比利斯迪纳摩,第比利斯迪纳摩熟悉欧洲足球的朋友们应该会了解,在冷战时代,苏联和东欧诸多国家有多支名为“迪纳摩”的球队,比较著名的如基辅迪纳摩、萨格勒布迪纳摩、德累斯顿迪纳摩,这些代表着国安系统的球队,在各自国家乃至欧洲足球史上都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这些球队或者只能在国内联赛称霸,或者在低级别联赛挣扎,大都难以重演往日辉煌。
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冷战时期在苏联足坛举足轻重的豪门第比利斯迪纳摩。从名字可以看出,这支球队当然隶属于内务部系统,但它又来自格鲁吉亚,因此在这支球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既有浓厚的内务部背景,又有鲜明的格鲁吉亚民族特色。苏联时代的第比利斯迪纳摩,成为政治斗争、民族政策、、社会文化、竞技体育等多种因素纠葛在一起的万花筒。
本文原名《足球艺术与秘密警察:格鲁吉亚足球在多民族的苏联帝国》(Soccer Artistry and the Secret Police: Georgian Football in the Multiethnic Soviet Empire)。
原作者:埃里克·R·斯科特(Erik R. Scott),堪萨斯大学教授,曾获得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博士学位,著作包括《熟悉的陌生人:格鲁吉亚犹太人及苏维埃帝国的演变》
译者:萨洛米·别尔泽尼什维利(Salome Berdzenishvili)和安东·瓦扎拉泽(Anton Vatcharadze)
本文收录于《全世界都在观看:冷战时期的体育运动》(The whole world was watching : sport in the Cold War)一书
在1960年第比利斯迪纳摩出版的一份官方球迷指南里,用非写实风格的漫画描绘了苏维埃格鲁吉亚足球队的球星,这些球星们一边唱歌,一边在足球上杂耍。这份球迷观赛指南的插画师有意地将格鲁吉亚足球与其热情奔放、丰富多彩且斗志昂扬的民族舞蹈风格联系起来,而后者恰恰是格鲁吉亚这个小小的加盟共和国在整个苏联都为人所知的特色。在其中一页中,球队前锋阿夫坦迪尔·戈戈贝里泽(Avtandil Ghoghoberidze)的形象是在足球上保持平衡的同时,用手表演格鲁吉亚舞蹈Kartuli,这种浪漫的舞蹈往往在婚礼上表演。整本球迷指南的内容都在暗示,格鲁吉亚足球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和格鲁吉亚民族舞蹈的特色动作,是同一个国家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足球和舞蹈的密切联系在两方面都起到了作用。大约在指南出版的同时,格鲁吉亚国家舞蹈团推出了一首舞蹈作品,有趣的是,在舞蹈表演内容也包括舞者在台上互相传球。
球迷手册中戈戈贝里泽的卡通形象
阿夫坦迪尔•戈戈贝里泽
足球是在苏联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它反映了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分野,而且有时候强化了这种分野。尽管足球运动获得了政府的支持,但它为苏联公民呈现了一系列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每个共同体都有自己的象征、英雄、神话和不满。在莫斯科,实力强大的俱乐部周围形成了不同的球迷团体,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莫斯科迪纳摩和莫斯科斯巴达克,前者得到了秘密警察部门和政府公务部门的支持,而后者则吸引了莫斯科的工会组织以及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拥护。各加盟共和国成绩出色的俱乐部成为某个区域的顶尖豪门,最突出的例子是基辅迪纳摩和第比利斯迪纳摩,事实上,这两家俱乐部分别成为获得乌克兰族和格鲁吉亚族大部分人支持的共和国代表队。
虽然整个苏联的各个俱乐部球队在取得成功时,都会因其技术风格和比赛效率而获得赞誉,但格鲁吉亚足球运动员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而闻名。莫斯科的各个球队有不同的球迷基础,但球迷们主要是为了获胜而欢呼,或者因为输球而口诛笔伐。基辅迪纳摩的球风与俄罗斯密切相关;队里有很多俄罗斯人,球队的教练多年来自莫斯科。同样,明斯克迪纳摩虽然不如基辅迪纳摩成功,但很难与俄罗斯的俱乐部区分开来;许多未能加盟莫斯科队的球员会前往明斯克。埃里温亚拉腊足球队(Ararat Yerevan,亚美尼亚首都球队)和巴库石油足球队(Neftyanik Baku,阿塞拜疆首都球队)偶尔会让莫斯科的球队感到不安,这些球队有时被认为表现出了某种“南方”气质,但他们的成功往往归功于技术和训练,而不是比赛方式。格鲁吉亚足球似乎给球迷提供了另一种明显的民族化选择,与整个苏联足球都迥然不同的风格。
格鲁吉亚足球的技术风格及其围绕的神话,是在集权的苏联国家和自信的格鲁吉亚共和国之间的碰撞中产生的。第比利斯迪纳摩这支格鲁吉亚最成功的球队的名字恰恰暗示了某种紧张关系:迪纳摩是由内务部系统管理的全苏体育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第比利斯是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的首都,也是20世纪格鲁吉亚农民大规模迁居的目的地。在第比利斯,当地政党领导人支持成立民间舞蹈团,汇集格鲁吉亚农村的舞蹈,并将其编排为具备鲜明特色的肢体动作。与此同时,格鲁吉亚首都豪门第比利斯迪纳摩汇集了共和国最优秀的球员,组建了一支能够代表整个共和国的占据统治地位的球队。莫斯科方面对这些事态的发展了如指掌。他们邀请格鲁吉亚舞蹈演员到克里姆林宫表演,以展示苏维埃国家对发展多样性民族文化的承诺,并征召第比利斯迪纳摩的优秀球员进入苏联国家队。格鲁吉亚的舞者和球员体现了这个加盟共和国的特殊性;莫斯科的决策者则试图保证格鲁吉亚差异的民族特色符合整个国家的需要。
20世纪40年代的第比利斯迪纳摩
格鲁吉亚足球可以说是国家的边疆与中央通过互动形成的混血儿,但是它仍然被视为整个苏联足球界的异类,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足球。格鲁吉亚球迷和体育运动从业者有意识地强调足球与民族舞蹈风格之间的联系,声称两者展现了同样的美、技艺和灵巧。对格鲁吉亚足球的定义偏离了其本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评论员都认为这是一种基于情感而非算计的足球,以盘带过人而非强硬防守为主,是创造性的艺术足球而不是野蛮的肉搏。然而,人们仍然认为格鲁吉亚球员可以成为全苏足球队的有效补充。
围绕格鲁吉亚足球的神话,因其与成绩出色、以“美丽比赛”风格著称的南美球队联系起来而更加鲜明。有趣的是,南美球员踢球的方式也被认为是舞蹈。阿根廷足球精妙的盘带让人想起探戈,而巴西足球明快的风格与桑巴有关。阿根廷队和巴西队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功令两国球迷感到自豪;这些胜利似乎证明了阿根廷混血文化和种族庞杂的巴西文化可以成功地对抗更强大、更发达国家的文化。足球将所谓落后的南美洲文化品质转化为现代化且全球性体育的资产。当地的足球从业者和球员往往会特意强调球队比赛风格的民族差异,而各国球迷也进一步认可了这种差异。
苏维埃格鲁吉亚也在通过足球寻求类似的认可,在球场上培养了一种民族独特性的神话,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神话符合格鲁吉亚以及整个苏联的目标。然而,像阿根廷人和巴西人一样,格鲁吉亚人也梦想着通过超越苏联边界的足球获得全球范围内的归属感。在冷战期间,格鲁吉亚足球运动员通过参与足球外交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了突出的地位,足球外交是苏联向后殖民时代进行全球拓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美国试图通过派遣数百名非裔美国运动员前往海外友好旅行,以此证明自己已经克服了种族问题,同时期的苏联则利用足球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和谐的多民族国家,饱受几百年殖民统治的广大后殖民国家面前,展示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形象。
本文考察了格鲁吉亚足球在20世纪的演变,阐述了第比利斯迪纳摩作为民族差异神话的化身,是如何在冷战背景下作为表达格鲁吉亚民族和苏联多民族团结的手段。通过本文内容可以看到,苏联对格鲁吉亚足球的推广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在球场上,格鲁吉亚民族和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有了新的含义,但这种意义并不总是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格鲁吉亚足球在苏联的大力推广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第比利斯迪纳摩的成功,最终被认为是格鲁吉亚民族的成功,而不是整个苏联的成就。
1948年的第比利斯迪纳摩队
与大多数国家的足球神话一样,格鲁吉亚的足球神话强调其悠久的历史渊源。事实上,格鲁吉亚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足球是从英国直接进口的,而不是从俄罗斯那里流出的二手货。大约在19世纪末,在英国企业家将足球引入莫斯科的同时,英国的实业家和工人通过黑海港口波季将足球带到了格鲁吉亚。足球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前就已经在格鲁吉亚流行开来,观察家们甚至在1925年第比利斯迪纳摩正式成立之前,就指出了这里的足球具备明显的民族风格。早在20世纪20年代,格鲁吉亚足球运动员就被冠之以“伟大的乌拉圭人”(didi urugvaelebi)的称号,这里既是借乌拉圭在足球界的统治地位,也指一种所谓的南方足球风格,这种风格重视艺术性而非纪律性,强调即兴发挥的进攻风格而非战术整体性。
然而,格鲁吉亚足球的代表第比利斯迪纳摩队是在斯大林时期建立的,并带有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老乡贝利亚的烙印,这并非巧合。在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倡议下,全联盟迪纳摩体育协会自成立以来一直与内务人民委员会联系在一起。作为格鲁吉亚内务部门的负责人,贝利亚在促进第比利斯迪纳摩成立之初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第比利斯迪纳摩首次参加比赛,并将贝利亚视为“一号荣誉会员”。第比利斯的迪纳摩体育场甚至以贝利亚的名字命名。
贝利亚在一些时候会大力支持这支家乡俱乐部。1939年,莫斯科斯巴达克队与第比利斯迪纳摩队之间的苏联杯半决赛被宣布结果无效并进行重赛。据斯巴达克队球员尼古拉·斯塔罗斯丁(Nikolai Starostin)所说,这个决定是“层次很高的、绝非体育界”领导做出的,很可能是来自贝利亚,贝利亚甚至在担任莫斯科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之后,仍继续担任第比利斯迪纳摩俱乐部的主席。尽管贝利亚已经入主中枢,但仍然是第比利斯迪纳摩的热情支持者,他的支持对于在格鲁吉亚建立持久的足球制度基础至关重要;在贝利亚的亲自过问下,第比利斯迪纳摩建设了一流的设施,并确保了这支球队在苏联足球世界中的相对优势地位。
不过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代表加盟共和国球队的民族特色被认为是倾向于附和了半官方的民族等级制度。在1949年莫斯科出版的一份观赛指南中,格鲁吉亚足球运动员“神经刀式”的比赛风格,因其“高度个性化的技术”和“引人入胜的战术组合”而受到赞誉,但这种令人兴奋的、冲动的打法与苏联守门员的神圣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的形象是坚韧不拔地准备抵御任何攻势。在这种情况下,第比利斯迪纳摩的守门员和教练往往是俄罗斯人,这一点很重要。格鲁吉亚球队经常被苏联媒体描述为一支发挥时好时坏的“喜怒无常的球队”。因此,在球门线和教练席上将华丽的格鲁吉亚艺术与钢铁般的斯拉夫纪律相结合,可能会让球队组织者觉得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方案。这样的安排在意识形态上也是恰当的,符合斯大林主义关于俄罗斯人民是苏联各民族老大哥的主张。
1953年,斯大林去世,随后贝利亚被其政治对手逮捕并处决,这是第比利斯迪纳摩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尽管球队的支持者被捕,但第比利斯迪纳摩在那一年的球场上仍然占据统治地位。9月4日,该队以2比1战胜莫斯科鱼雷队,几乎摸到了苏联顶级联赛冠军的奖杯。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人们回忆起1939年莫斯科斯巴达克队在苏联杯比赛中与迪比斯利迪纳摩的重赛事件。这一次第比利斯迪纳摩队的胜利也被宣布无效。苏联媒体报道,由于迪纳摩队两名球员的“粗暴行为”,这场比赛被要求重赛。重赛的决定来的相当迅速,有一种说法是,当时苏联的领导人认为,在贝利亚面临叛国指控的同时,让格鲁吉亚球队获得冠军头衔,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三天后,沮丧的第比利斯迪纳摩队输掉了与莫斯科鱼雷队的重赛,与冠军失之交臂。格鲁吉亚球迷,不管对贝利亚的看法如何,无疑都会觉得是中央政府抢走了他们的冠军。
考虑到这支球队与斯大林时代高官的密切联系,第比利斯迪纳摩队在斯大林去世和贝利亚被处决后的转变相当惊人。尽管它仍然是内务系统赞助的迪纳摩组织的一部分,但接下来体育场被改名,球迷指南中和贝利亚有关的所有痕迹都被抹去,这支球队实际上从斯大林主义政策的载体变成了后斯大林时代格鲁吉亚男子气概最理想的象征。随着斯大林之后,格鲁吉亚人从苏联高层消失,第比利斯迪纳摩的球员成为格鲁吉亚人的新一代英雄,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球队成为表达对这个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央表达不满的方式。
在后斯大林时期,球迷的经历也在发生变化。球迷文学作品大量涌现,格鲁吉亚足球成为流行电影的主题,这些电影神话了格鲁吉亚足球在十月革命前的起源,并展示了其支持者的极度忠诚,电视转播的比赛吸引了更多观众,球迷可以在整个苏联的电视屏幕上观看第比利斯迪纳摩的比赛。为了强调球队独特的艺术性,第比利斯迪纳摩队比赛转播中,最著名的播音员是来自格鲁吉亚的著名戏剧演员科特·马克哈拉泽(Kote Makharadze),他强有力的表达方式、充满诗意的措辞以及浓重的俄语口音,将格鲁吉亚人的身体文化与风格鲜明的声音联系起来。1964年,第比利斯迪纳摩队首次成为苏联顶级联赛冠军(该队分别于1939年、1940年、1951年和1953年获得亚军),也因此获得了一首新歌。由在苏联广受欢迎的格鲁吉亚乐队Orera录制,这首名为“chveni orkros bichebi”(我们的金童队)的歌曲中提到“实现梦想”和“斩获进球”,但却没有提到苏联或社会主义。这首歌以吉他弹奏,采用了传统的格鲁吉亚复调和声,既有现代元素又植根于民族文化。
1964年苏联冠军第比利斯迪纳摩队全家福
由于格鲁吉亚足球从业者的推动,为格鲁吉亚足球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神话,符合第比利斯迪纳摩球星的风格,他们这种格鲁吉亚民族独特性的主张引发了格鲁吉亚球迷的共鸣。虽然还有其他势均力敌的格鲁吉亚俱乐部获得了当地球迷的热情支持,比如库泰斯鱼雷队(Torpedo Kutaisi),但只有第比利斯迪纳摩队能够在冠军争夺战中一骑绝尘,成功赢得苏联全国冠军。这支球队在共和国之外代表着格鲁吉亚足球,与俄罗斯队相比,其民族特色更加突出。尽管这项运动最早是外国传入的,并且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支持而取得了进步,但第比利斯迪纳摩在足球场上的成功,被视为是格鲁吉亚民族艺术天赋的组成部分。
冷战期间,苏联在国际观众面前展示格鲁吉亚足球的魅力,让格鲁吉亚足球运动员得以在苏联国家队闪亮登场,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首次亮相。入选苏联国家队的人选要符合两个重要的标准,甚至说这两个标准有点自相矛盾,首先这支球队必须反映苏联这个国家多民族联盟的理想,也就是兄弟般的“各民族人民的友谊”,而且必须成功地体现民族团结。在“人民友谊”的图景中,俄罗斯人通常被赋予主导地位,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民族则处于辅助地位,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这意味着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共同体。
因此,一支理想的苏联国家队,可能是由俄罗斯人担任关键位置,并获得来自苏联另外15个加盟共和国的非俄罗斯族球员的配合(虽然球场上只有11个位置,但人们认为较小的共和国也可以输送替补球员)。事实上,参加奥运会和世界杯的苏联队看起来截然不同。来自莫斯科各俱乐部的球星,以及成绩出色的基辅迪纳摩队和第比利斯迪纳摩队的球员,统治着苏联国家队,这反映了苏联足球发展的不均衡。尽管格鲁吉亚人口只占苏联总人口的2%,但他们在国家队的比例始终特别高。对于第一支苏联奥运足球队来说,第比利斯迪纳摩输送的球员数量位列第二,总计六人。1958年,当苏联首次参加世界杯时,来自第比利斯迪纳摩的格鲁吉亚球员占全队的五分之一,而且这种势头一直维持到苏联解体。苏联国家队第一次出现非莫斯科俱乐部出身的队长是在1972年,当时由第比利斯迪纳摩的后卫穆尔塔兹·库尔奇拉瓦(Murtaz Khurtsilava)掌舵。第二次是在1980年,当时他的第比利斯队友亚历山大·奇瓦泽(Aleksandre Chivadze)担任国家队队长。
亚历山大•奇瓦泽正在和马拉多纳拼抢
亚历山大•奇瓦泽
苏联通常会把国家队由来自莫斯科球队,以及基辅迪纳摩和第比利斯迪纳摩的球员统治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家队主教练加夫里尔·卡恰林(Gavril Kachalin)撰写的一份关于苏联队在1970年世界杯上表现的报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该报告承认,苏联队的“核心”仅由四家俱乐部的球员组成:莫斯科斯巴达克、基辅迪纳摩、第比利斯迪纳摩和莫斯科中央陆军。而那些球员很少入选国家队的共和国足协,经常会抱怨自己在国家队缺少代表人物。相比之下,格鲁吉亚足球界则吹嘘他们作为南方共和国取得的成功。在1970年的苏联足协会议上,格鲁吉亚代表茨玛亚建议其他共和国可以借鉴格鲁吉亚足球的比赛风格:“也许大家都可以按照我们共和国的方式进行比赛。我们为苏联各年龄段国字号球队输送了大批球员。”茨玛亚的吹嘘态度激怒了足协主席瓦连京·格拉纳钦(Valentin Granatkin),他断喝道:“那是因为你们那地方没有冬天!”
更紧迫的问题是苏联队在国际比赛中成绩不够突出。仅在1966年闯入世界杯半决赛,以1比2的比分输给西德队。尽管苏联媒体一直称赞国家队在比赛中体现的团队精神,苏联球迷还是梦想国家队能够将斯拉夫球员的自律和运动风格与格鲁吉亚人的灵巧和创造力有机结合起来,但这支球队从未真正团结起来。苏联国家队存在的问题是任何国家队都面临的问题:很难协调国家和俱乐部比赛的日程安排,而且俱乐部级别的赛事组织更稳定也更周密。然而,在苏联的大背景下,官员越来越担心国家队存在的缺点破坏了多民族和谐的意识形态。苏联当局的另一个方案,是向国外推广苏联更具凝聚力的俱乐部球队。苏联俱乐部在国际赛事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1975年基辅迪纳摩队击败欧洲顶级球队,赢得了欧洲优胜者杯和欧洲超级杯。基辅迪纳摩的成功促成了苏联体育界的一项计划,将乌克兰俱乐部打造为苏联国家队的基础。然而,事实证明,基辅迪纳摩并不是苏联的理想代表。基辅迪纳摩的特点很难与其主帅瓦列里·洛巴诺夫斯基(Valeri Lobanovskii)剥离开,后者以超理性的足球方式而闻名。这种名声可能并不完全名副其实,但这种将主教练以及他的球队捆绑在一起的刻板印象非常流行。在国际上,洛巴诺夫斯基似乎证实了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的恶意评价:外国记者形容他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嘲笑他的球员是“人造卫星”和“俄罗斯机器人”。基辅迪纳摩的球员几乎不可能同时满足国家队和俱乐部的需要。他们肩负着额外的比赛和训练的负担,消耗太大。1978年,以基辅迪纳摩为基础组建的苏联队在历史上首次未能晋级世界杯决赛圈。
虽然第比利斯迪纳摩从未像基辅迪纳摩那样统治过苏联足球,但格鲁吉亚球队的鲜明特点可以更好地满足冷战时期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需求。与乌克兰球队不同,第比利斯迪纳摩的明星被赋予了色彩斑斓、个性鲜明的标签。作为苏联的非俄罗斯和非斯拉夫代表,第比利斯迪纳摩的球员被要求担任与后殖民国家沟通的文化大使,并被派往拉丁美洲国家,这些国家被认为与格鲁吉亚的南方足球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格鲁吉亚球队的表现一般来说都不负众望。他们在巴西和阿根廷的表演赛中赢得了球迷的欢呼。1961年,阿夫坦迪尔·戈戈贝里泽与第比利斯迪纳摩的其他球员被派往古巴,受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接见。来访的格鲁吉亚球员给卡斯特罗戴上了传统的格鲁吉亚式帽子后,然后与卡斯特罗集体合影。另外一张更著名的照片拍摄于1965年苏联国家队与巴西国家队的友谊赛结束之后,照片中,苏联队的四位格鲁吉亚球星安佐尔·卡瓦扎什维利(Anzor Kavazashvili)、米哈伊尔·梅斯基(Mikheil Meskhi)、斯拉瓦·梅特雷维利(Slava Metreveli)和格奥尔吉·西奇纳瓦(Giorgi Sichinava)与足球巨星、赤膊上阵的贝利手挽手。这张照片在苏联媒体广泛传播,展示了格鲁吉亚人对巴西足球传奇人物的钦佩,但也将苏联队的格鲁吉亚人与据称在全世界无处不在的南方足球风格联系起来。
从原则上说,第比利斯迪纳摩的拥趸希望突出格鲁吉亚民族的独特性,同时传达苏联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在某些时刻,个人、民族和全苏的利益是一致的:根据大多数人的说法,格鲁吉亚足球运动员最初渴望满足国家的需要,特别是因为国际旅行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普通苏联公民无法进入的大门。戈戈贝里泽激动不已地回忆1954年他第一次访问巴黎时的情景,“在那些年,甚至在那之后,‘国际比赛’这个词仿佛都弥漫着一种魔力。”
在几十年后,第比利斯迪纳摩队在国内和国际取得的成功让球员和支持者获得了更大的信心。该队在1979年获得了第二个苏联顶级联赛冠军,并在1976年和1979年赢得了苏联杯。第比利斯迪纳摩也把他们独特的比赛风格带入国际舞台,试图在欧洲顶级俱乐部中占据一席之地,因为苏联官员和足球运动员也承认,这些欧洲俱乐部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其他俱乐部的标杆。因此,在1979年第比利斯迪纳摩队在9万名欣喜若狂的球迷面前,在主场3比0战胜利物浦队,这场比赛被誉为一项标志性的成就。随后,格鲁吉亚记者骄傲地引用了利物浦主帅鲍勃·佩斯利的说法,称第比利斯迪纳摩队的经济水平“让他惊喜”。(1979年的欧洲冠军杯第一轮比赛中,第比利斯迪纳摩先是在客场1比2不敌利物浦,在10月3日的主场比赛中3比0取胜。但在下一轮的比赛中,第比利斯迪纳摩队主客场被汉堡队双杀而被淘汰。)
第比利斯迪纳摩主场迎战利物浦的海报
第比利斯迪纳摩在接下来的赛季继续取得了俱乐部历史上最高的荣誉,击败卡尔蔡斯耶拿队赢得1981年欧洲优胜者杯冠军。诚然,这项赛事的分量不如欧洲冠军杯,决赛的对手是来自社会主义阵营东德的球队,而不是来自西欧的著名豪门。尽管如此,这个冠军对在国际足球比赛中战绩不佳的苏联乃至格鲁吉亚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苏联政府和球队的格鲁吉亚球迷都试图从这场胜利中分到一些奖励。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写道,“我们对他们(第比利斯迪纳摩)的支持没有落空”,并声称这场胜利是整个苏联的胜利。然而,格鲁吉亚人将球队的成功视为民族的胜利。居住在苏联各地的格鲁吉亚人纷纷来信来电祝贺球队,其中包括一位居住在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ASSR)的妇女,她宣称:“从此,欧洲足球将用格鲁吉亚口音对话。”
1981年优胜者杯的折桂似乎为第比利斯迪纳摩提供了一个超越苏联多民族阶层的机会,甩掉一直以来“发挥不稳定”的标签。1964年,当俱乐部获得了第一个苏联顶级联赛冠军时,第比利斯迪纳摩“金童队”的成功,与他们的俄罗斯教练加夫里伊尔·卡恰林紧密有关。尼古拉·斯塔罗斯丁认为,卡恰林通过“增强球队心理力量”的办法,“巧妙地引导这支进攻犀利但常常头重脚轻的球队取得成功”。然而,1981年夺冠的第比利斯迪纳摩由格鲁吉亚本土教练诺达尔·阿哈尔卡西(Nodar Akhalkatsi)掌舵。在第比利斯迪纳摩队夺取优胜者杯后,《真理报》的记者回顾了这支球队曾经神经刀式的风格:“早些时候,第比利斯迪纳摩队经常被称为发挥无常的球队,能够以出色的风格击败强大的对手,然后又会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输给一支更弱的球队。”而现在,据俄罗斯足球名记瓦伦丁·伊万诺夫(Valentin Ivanov)报道,这支球队终于把“长期以来创造性的技术发挥”与有效的组织“粘合”在一起。
回到格鲁吉亚时,第比利斯迪纳摩的球员们被热情的球迷抬下飞机,当他们在数万名涌入主场的球迷面前举起奖杯展示,这些球员被当成民族英雄。苏联格鲁吉亚乐队Iveria录制了一首庆祝夺冠的歌曲,融合了摇滚风格和格鲁吉亚复调,纪念这次球队的大胜利。这首歌的格鲁吉亚语歌词毫无疑问展示了这支球队的民族特点。歌词中赞扬第比利斯迪纳摩的“男孩”,他们的胜利“赞美了格鲁吉亚”;他们的成功就像高加索国家的“高山和山谷闪耀着光芒”。1981年国家队的球星之一达维特·基皮阿尼(Davit Kipiani)也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将国际比赛描述为证明格鲁吉亚民族性格的力量和活力的舞台。基皮阿尼在接受格鲁吉亚记者采访时解释道,“值得记住的是,足球不仅仅是由假动作、盘带和传球组成的。足球也是一场不同特点和个性之间的比赛。而性格类型在本质上体现的是民族性。”
第比利斯迪纳摩的成功,揭示了苏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通过格鲁吉亚足球来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对于格鲁吉亚以外的一些苏联观察员来说,第比利斯迪纳摩的成就及其球迷的行为,代表着对俄罗斯统治地位和泛苏联民族团结的日益挑战。虽然格鲁吉亚球员继续因为对苏联国家队的贡献而受到重视,但第比利斯迪纳摩队对那些来自苏联更大的加盟共和国的对手取得胜利,有时会引发民众的不满。
第比利斯迪纳摩的格鲁吉亚球迷因为许多莽撞甚至有时候有些出格的行动,在这个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里颇有些名气。在1971年苏联足协的一次会议上,格鲁吉亚代表公开反对在《苏联体育报》上对第比利斯迪纳摩球迷的粗暴描述,这篇报道称球迷“过于膨胀和情绪化”。与此同时,格鲁吉亚体育官员试图在国家队征召格鲁吉亚球员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想保护第比利斯迪纳摩的利益。也是在同一次足协会议上,格鲁吉亚代表将该问题定性为国家主权问题。这位代表解释说,足协有权“推荐”球员,但“向一个拥有自己宪法的主权共和国的体育委员会提出要求是不公平而无礼的。”
据说,在格鲁吉亚共和国境内,第比利斯迪纳摩的政治背景也通过非正式的办法协助球队管理。当时球队最有希望的门将安佐尔·卡瓦扎什维利(Anzor Kavazashvili)试图离开俱乐部前往俄罗斯踢球时,被限制购买飞机票,不得不伪装离开格鲁吉亚,盗用以朋友的名义购买的机票。格鲁吉亚克格勃甚至派代表前往列宁格勒追踪他,追到了他下榻的公寓。尽管格鲁吉亚当局在卡瓦扎什维利正式开始在俄罗斯踢球后就松口了,但他们还是利用一些办法诱使他回归。在为莫斯科斯巴达队效力期间,卡瓦扎什维利接到了来自第比利斯迪纳摩的足球运动员吉维·乔赫利(Givi Chokheli)的电话,乔赫利曾与他一起在苏联国家队踢球。格鲁吉亚体育部门主管要求乔赫利以私人身份劝说这位门将,他问卡瓦扎什维利:“难道你不想让自己的父母安享晚年吗?”卡瓦扎什维利几乎差点被劝动了,但当他得知无法保证在第比利斯迪纳摩的主力位置时,最终还是拒绝了邀请。
安佐尔•卡瓦扎什维利
第比利斯迪纳摩的球迷一直担心,国际上更加认可这支球队成为苏联而不是格鲁吉亚的代表。苏联的观众很容易辨认格鲁吉亚的民族特色,将格鲁吉亚独特的足球风格与舞蹈联系在一起。然而,苏联试图利用格鲁吉亚足球向国外传递这个这个国家的多民族多样性,取决于在国际舞台究竟是否理解这些民族的特点。一些外国人理解格鲁吉亚足球的这一特点,例如曾有一个法国记者将1964年的第比利斯迪纳摩队描述为“南美足球传统在东方最杰出的代表”。然而,国际人士并不总是能认识到格鲁吉亚球队在球场上的民族差异,一些格鲁吉亚球迷担心苏联的支持会导致外国人将这支球队视为俄罗斯球队。比如说1981年,西汉姆联队的官方通讯等出版物总之将取胜的第比利斯迪纳摩队称之为“俄罗斯人”和“苏联人”时,格鲁吉亚球迷尤其感到愤怒,仿佛这两个词是等价的。在苏联之外,将俄罗斯和苏联混为一谈是很常见的,但因为苏联公民是按加盟共和国来区分的,他们认为国家的区别是重要的,格鲁吉亚球迷将没有得到外国认可的现状,归咎于他们的团队,以及他们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无法真正独立。
1990年,第比利斯迪纳摩退出了苏联足协,俱乐部更名为第比利斯伊比利亚(后来又改回了第比利斯迪纳摩),这是格鲁吉亚东部的古国。格鲁吉亚足球追求在独立于莫斯科的国际舞台上取得成功,与争取国家主权息息有关。1990年11月,一名格鲁吉亚记者在共和国的主要报纸上写道,苏联足协是一个“帝国组织”,阻碍了格鲁吉亚“进入国际舞台”,他指出,格鲁吉亚人被迫接受外国媒体的报道,称格鲁吉亚共和国这支著名球队是一群“俄罗斯表演家”组成的。尽管苏联的内务部门支持并推动了第比利斯迪纳摩俱乐部的发展,但格鲁吉亚足球反而成为推进民族主义分离的平台。
1990年3月30日,格鲁吉亚锦标赛的第一场比赛。格鲁吉亚未来的总统兹维亚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在迪纳摩球场向观众发表讲话
未能组建一支真正成功的代表全苏的球队,反映了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内部的紧张局势,这在后斯大林主义时期变得更加明显。由于各加盟共和国试图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推动自己的目标,中央体育部门不得不在各个政府部门支持的球队之间进行协调,因此,组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国家队变得愈发困难。当局依赖共和国级别的球队在国外代表苏联,这必然会引发不满,因为莫斯科通过投入资金和强化基础设施推动了这些运动队的进步,但代价是要控制他们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并声称他们通过比赛获得了收益。
格鲁吉亚足球运动员在为苏联踢球时获得了国际知名度,因此他们寻求更多的独立性和更高的薪水。在这些野心的推动下,格鲁吉亚于1988年成立了苏联第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第比利斯姆雷特比(Mretebi Tbilisi)。然而,后苏联时代格鲁吉亚足球的严酷现实使南美式足球天堂的梦想越来越远,在1991年的电影《我是贝利的教父》(me, peles natlia)中反映了这一变化。在电影中,一名格鲁吉亚中年男子神奇地穿梭在破败的第比利斯和充满足球传奇、衣着暴露的女性和狂欢节的奢华巴西之间。他回来时讲述了他如何与贝利的父亲成为朋友,并教他的儿子,巴西足球传奇贝利踢球;然而,在第比利斯,他的妻子对此无动于衷,他的债主对他穷追不舍,而他仍被困在工作岗位上,只是一个负责检查格鲁吉亚摇摇欲坠的电力基础设施的低级别工作人员。事实上,大多数具有足球天赋的格鲁吉亚人都离开了这个国家;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更准确地说,它们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因为有些是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开始的),冷战的结束使球员更容易转会到更为知名的外国球队,也更加有利可图。在经历了1991年至1993年的格鲁吉亚内战,并目睹了国家经济的崩溃之后,第比利斯姆雷特比的希望之星格奥尔基·金克拉泽最终以约200万英镑的转会费加盟曼城。
虽然足球与民族性格之间的联系一直很微弱,但在后冷战时代,足球越来越难以视为民族性格的代表。老牌俱乐部被外国投资者收购,球星被出价最高的人买走,这使得英超联赛变成了一个全球化运营的联赛,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球员是英国人。欧洲的各个国家队也变得更加多元化,吸引了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和少数民族;许多人赞扬这些球队体现了多元文化,但也有人批评他们没有达到民族同质性的期望。到了21世纪初,甚至连巴西国家队所体现的巴西风格这个概念,都不能反映球队在球场上的技术风格,更像是与成功的全球化文化有关的神话。在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人试图将足球重新做为独立国家的代表,但比赛规则已经改变了。
参考文献
[1] N. Dumbadze, M. Karchava, Z. Bolkvadze, and G. Pirtskhalava, “Dinamo” Tbilisi (Tbilisi: Soiuz zhurnalistov Gruzii, 1960).
[2] Dekada gruzinskogo iskusstva i literatury v Moskve: Sbornik materialov (Tbilisi: Zaria vostoka, 1959), 247.
[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4] Robert Edelman, “A Small Way of Saying ‘No’: Moscow Working Men, Spartak Soccer,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1900–1945,”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 no. 5 (2002): 1441–1474.
[5] On Dinamo Kiev, see Manfred Zeller, “‘Our Own Internationale,’ 1966: Dynamo Kiev Fans between{not capitalized in original title} Local Identity and Transnational Imagination,”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12, no. 1 (2011): 53–82.
[6] I am grateful to Robert Edelman{changed to be consistent with other endnote entries} for his observation regarding Dinamo Tbilisi’s name.
[7] On the history of Georgia’s folk-dance ensembles, see Erik R. Scott, Familiar Strangers: The Georgian Diaspora and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Empi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8] On the cultivation of football by Soviet and post-Soviet political leaders, see Régis Genté and Nicolas Jallot, Futbol: Le ballon rond de Staline a Poutine, une arme politique(Paris: Allary Éditions, 2018). The book’s authors, French journalists, draw on an earlier, unpublished version of this essay, as well as a podcast interview I gave in 2015, in their discussion of Georgian football. For the interview, see Erik R. Scott, “Georgian Football,” Sport in the Cold War (podcast), episode 8, December 2015,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resource/sport-in-the-cold-war/episode-08-georgian-football.
[9] The term “beautiful game” entered international parlance with Brazil’s victory in the 1958 World Cup. Richard Giulianotti, Football: A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Gam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9), 26.
[10] Eduardo P. Archetti, Masculinities: Football, Polo, and the Tango in Argentina (Oxford: Berg, 1999); Roger Alan Kittleson, The Country of Football: Soccer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Brazi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11] Archetti, Masculinities, 162.
[12] Damion Thomas, “Playing the ‘Race Card’: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in East Plays West: Sport in the Cold War, ed. Stephen Wagg and David L. Andrews (London: Routledge, 2007), 207–221.
[13] Otar Gagua, Boris Paichadze, ed. D. Kvaratskhelia, trans. G. Akopov (Tbilisi: Ganatleba, 1985), 10.
[14] Mindia Mosashvili, maradiuli dghesastsauli [The Eternal Holiday](Tbilisi: khelovneba, 1982), 25.
[15] The term chekist came from a predecessor to the NKVD, the VChK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and continued to be used to refer to those who worked for the NKVD’s successor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KGB (Committee for State Security).
[16] Otchety o rabote otdelov TsK KP Gruzii, 1936, sakartvelos shinagan sakmeta saministro arkivi [Archive of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of Georgia], Tbilisi, f. 14, op. 8, d. 172; Futbol’naia komanda “Dinamo” Tbilisi (Tbilisi: Izdatel’stvo Gruzpromsoveta, 1940).
[17] Nikolai Starostin, Zvezdy bol’shogo futbola (Moscow: Fizkul’tura i sport, 1969), 68–74.
[18] Nashi futbolisty: Dinamo Tbilisi (Moscow: Fizkul’tura i sport, 1949), 8. On the Soviet goalkeeper, see Mike O’Mahony, Sport in the USSR: Physical Culture—Visual Culture(London: Reaktion, 2006), 140–144.
[19] Gagua, Boris Paichadze, 100.
[20] Sovetskii sport, September 8, 1953.
[21] Drawing on his interview with Aksel’ Vartanian, Robert Edelman advances this argument in Spartak Moscow: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Team in the Worker’s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207–209.
[22] The movies referenced arepirveli mertskhali [The First Swallow] (1975) and burti da moedani [Ball and Pitch] (1961).
[23] “chveni okros bichebi!” [“Our Golden Boys!”] YouTube, June 14, 20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pUKGOG51KI.
[24] Proekty postanovlenii po voprosam podgotovki sovetskikh sportsmenov k Olimpiade v Khel’sinki, February 21, 1952,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sotsial’no-politicheskoi istorii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 (RGASPI), Moscow, f. 17, op. 132, d. 571.
[24] Materialy zasedanii prezidiuma Federatsii futbola SSSR, 1969, Gosudarstvennyi arkhiv Rossiisskoi Federatsii [State Archiv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GARF), Moscow, f. R-7576, op. 31, d. 296, l. 75.
[25] Materialy zasedanii prezidiuma Federatsii futbola SSSR, 1969, Gosudarstvennyi arkhiv Rossiisskoi Federatsii [State Archiv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GARF), Moscow, f. R-7576, op. 31, d. 296, l. 75.
[26] See, for example, Stenogramma otchetno-vybornogo plenuma Soveta Federatsii futbola, January 25, 1968, GARF, f. R-9570, op. 4, d. 87, ll. 61–112.
[27] Stenogramma plenuma Soveta Federatsii futbola SSSR, February 4, 1970, GARF, f. R-7576, op. 31, d. 660, ll. 25–51.
[28] Robert Edelman, Serious Fun: A History of Spectator Sports in the USS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6.
[29] Lobanovksii is defended in Hans-Joachim Braun and Nikolaus Katzer, “Training Methods and Soccer Tactics in the Late Soviet Union: Rational Systems of Body and Space,” in Euphoria and Exhaustion: Modern Sport in Soviet Culture and Society, ed. Nikolaus Katzer, Sandra Budy, Alexandra Köhring, and Manfred Zeller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Verlag, 2010), 269–294.
[30] Ibid., 283.
[31] Edelman, Serious Fun, 175.
[32] Valentin Bubukin, “Gody letiat bystree miachei,” Sportivnaia zhizn’ Rossii 8 (2005).
[33] Avtandil Gogoberidze, S miachom s trideviat’ zemel’ (Tbilisi: Soiuz zhurnalistov Gruzii, 1965), 142.
[34] Ibid., 48.
[35] Federatsiia sportivnykh zhurnalistov Gruzii, Voskhozhdenie kubku: spravochnik (Tbilisi: TsK KP Gruzii, 1981), 56–57.
[36] Ibid., 104.
[37] Starostin, Zvezdy bol’shogo futbola, 308.
[38] Federatsiia sportivnykh zhurnalistov Gruzii, Voskhozhdenie kubku, 95.
[39] Ibid., 91.
[40] dinamo-dinamo,” YouTube, October 24, 200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lUX37PMw8o {lower-case “d” should be kept as it reflects Georgian usage}
[41] Guram Pandzhikidze, Dinamo, Dinamo, Dinamo!,trans. S. N. Kenkishvili (Rostov-on-Don: SKNTs VSh IuFU, 2011), 55–56.
[42] Stenogramma plenuma Soveta Federatsii futbola SSSR, January 25, 1971, GARF, f. R-7576, op. 31, d. 1013, l. 96.
[43] Ibid., l. 94.
[44] Anzor Kavazashvili, Ispoved’ futbol’nogo maestro (Moscow: Ianus-K, 2010), 35.
[45] Ibid., 49.
[46] Alastair Watt, “Dinamo Tbilisi and the Quest for the Champions League,” Futbolgrad, July 14, 2014, http://futbolgrad.com/dinamo-tbilisi-quest-champions-league.
[47] Ibid.
[48] Edelman, Serious Fun, 241–242
[49] Leonard Shengelaia, “O futbole, i ne tol’ko o nem,” Zaria vostoka,November 28, 1990.
[49] “Kak tbilisskoe ‘Dinamo’ kinulo ‘Mretebi,’” Tribuna, February 27, 2013, http://www.sports.ru/tribuna/blogs/sixflags/427739.html.
[50] “Kak tbilisskoe ‘Dinamo’ kinulo ‘Mretebi,’” Tribuna, February 27, 2013, http://www.sports.ru/tribuna/blogs/sixflags/427739.html.
[51] David Clayton, Everything Under the Blue Moon: The Complete Book of Manchester City FC—and More! (Edinburgh, UK: Mainstream, 2002), 122.
[52] “State of the Game: How UK’s Football Map Has Changed,” BBC News, October 10, 2013, https://www.bbc.com/news/uk-24464020
[53] See Lindsay Sarah Krasnoff, The Making of Les Bleus: Sport in France, 1958–2010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3).
[54] See Kittleson, The Country of Football, 165–211
最新热门赛事
 591
591
 427
427
 425
425
 471
471
 423
423
 401
401
 415
415
 403
403
 401
401
 598
598